沉寂数百年的石阶破损狰狞,缺口处渗透着风干的暗红色血迹,真是奇怪……这有违规律。
旅人的靴子踏上去,漆黑如墨般的苔藓予人泥泞的触感,旅人吐了吐舌头。
“像咖啡色的奶油布丁。”
作呕的笑话,你这么想着。用银剑挑起一点苔藓凑近观察,像是用丛林孢子那样怪异的东西培育的杂交种。
“勇者大人,这不是舞会的红毯,我想希芙拉的祭祀应该是一个色盲。”
你沉吟着,并不想接话。抬头向上望去,幽黑的洞窟内壁生长着不符合规律的石钟乳。
你忽有一种恍惚,石钟乳的尖端变得错综扭曲,湿润粘滑的质感下宛若缠绕在肠道内壁的绒毛,从四面八方挤压着这庞大的祭祀台。
看起来真像一个巨大生物的消化道啊。
旅人似乎有新的进展,掏出随身的刷子,换过一头开始敲打石砖。
“勇者啊,你听到了什么?”
没有音律,甚至都没有节奏,只是胡乱敲打发出的声响……
你淡淡地看了一眼旅人,思考着应该如何劝告他那近乎愚蠢又迷惑的行为。
令人牙酸的声音从祭祀台下方传来,不,正确来说是周边深不见底的下方,该死的,他引来什么了?
——
苍白之焰从亡者枯骨上燃起,亡魂倾听嘈杂之音循声而来,既无目的,又无选择,骸骨将痴愚地行军。
——
一只只白骨的手爪攀附在墙壁上,骨骼磨蹭声刺耳又诡异,骷髅们循声而来,似乎并未觉察有生者到来,仅是用尽剩余的本能来到此地。
旅人迅速起身,按住你将要出鞘的银剑,你并非不解,回望一眼,不知什么时候起旅人的斗篷内散发着一股幽暗蓝光。
旅人将蓝光的源头丢出——水蜡烛在浑浊空气中扶光而落,亡者纷纷扑向蓝光,霎时间,骨片四处飞溅。
难以想象,这究竟是仇恨还是朝拜。
“不明之物的赐福替代了诅咒,尼尔霍斯的骨骼愈发庞大,以至于皮肉都开始崩解,躁狂的力量蒙蔽了他的双眼,使他无法认清伟大与渺小,不明所以地四处行军,周遭的军队都会躲避着他的疯狂,‘勇猛的王啊,您那不朽的伟力足以让铁骑人马俱亡,猛兽开肠破肚,堡垒坍陷毁灭,可您为何不看看这是否是我们的领土呢?’他的第二位妻子娜尔雅安向那片阴影祈祷‘不朽的主啊,赐给我视域吧,我需要它为您拨清迷雾’,娜尔雅安肚中的孩子化为血水,一根脐带被她排出体外,阴影中的存在让她将此代替神经链接在尼尔霍斯的双眼上,痴愚的领主恢复了澄澈,他在无人知晓的角落里点燃了蜡烛,如水般幽暗的蓝光下他想要去看清阴影,宛若窥视昏暗房间的幼童。”
旅人如是说,你并没有摆出实质性的态度。
令人感叹,仅此而已。
希芙拉的灭亡与此无关,至少这位愚昧的领主还没有疯狂到毁灭一切。
你冷眼看着还在蠕动的骸骨,将圣粉挥洒于阴湿空气中,腐臭与冷冽穴风交织,气滞流淌在鼻间。
“我宁愿你用臭虫剑处决我。”
旅人捏紧鼻子不满地抱怨。
探索似乎被卡入一个死胡同了,这里没有通道与天窗,只有庞大得堪称神迹的祭祀台。
“希芙拉是地底之城呢,我睿智的勇者啊。”
旅人笑笑靠近,似乎在试图说服你下坠于幽坑中。
你从石台下拾取一根蜡烛,用银剑磨蹭出火花,一缕新生的焰苗诞生于幽暗洞窟中,但不幸地是,你将它丢下了幽坑中。
“哐当……”
火焰依旧闪烁着,旅人趴在断崖上扯着脖子看。
“没有尸油,没有骨块,只有静默的碑文。勇者啊,我们好像真的需要下去看看呢。”
你没有说话,不顾旅人的反对,将绳子捆在他的身上,并缠绕在一根石柱上作为锚点。
“喂喂!不要这样!我已经认可了自己观光旅游团的身份啊!”
你没心情去听这近乎于无赖的理由,因为貌似有一群不欢迎你们的猎犬正在靠近。
——
无瑕者的触碰赋予它们亘古的时间,在幽黑空洞中寻觅着替死的生灵,悼亡者在祈祷,骷髅的头颅飞翔般携带着诅咒。
——
淡蓝色幽光于洞壁上浮现,似油墨滴于焦炭间粘稠。
骷髅头颅挣扎着脱离触手般的石钟乳,向闯入者坠落;宛若宫殿般的祭祀台下再次攀爬出白骨,这次不同的是,它们裹挟着盔甲含着锈蚀铁剑,狰狞地行进;用于祭祀的礼袍凭空悬浮,骨架支撑着,喷吐着火焰。
你后退一步,希芙拉的面孔正在一步步被揭露。
好吧,原来一直鸽子,咳咳,我的错
沉寂数百年的石阶破损狰狞,缺口处渗透着风干的暗红色血迹,真是奇怪……这有违规律。
旅人的靴子踏上去,漆黑如墨般的苔藓予人泥泞的触感,旅人吐了吐舌头。
“像咖啡色的奶油布丁。”
作呕的笑话,你这么想着。用银剑挑起一点苔藓凑近观察,像是用丛林孢子那样怪异的东西培育的杂交种。
“勇者大人,这不是舞会的红毯,我想希芙拉的祭祀应该是一个色盲。”
你沉吟着,并不想接话。抬头向上望去,幽黑的洞窟内壁生长着不符合规律的石钟乳。
你忽有一种恍惚,石钟乳的尖端变得错综扭曲,湿润粘滑的质感下宛若缠绕在肠道内壁的绒毛,从四面八方挤压着这庞大的祭祀台。
看起来真像一个巨大生物的消化道啊。
旅人似乎有新的进展,掏出随身的刷子,换过一头开始敲打石砖。
“勇者啊,你听到了什么?”
没有音律,甚至都没有节奏,只是胡乱敲打发出的声响……
你淡淡地看了一眼旅人,思考着应该如何劝告他那近乎愚蠢又迷惑的行为。
令人牙酸的声音从祭祀台下方传来,不,正确来说是周边深不见底的下方,该死的,他引来什么了?
——
苍白之焰从亡者枯骨上燃起,亡魂倾听嘈杂之音循声而来,既无目的,又无选择,骸骨将痴愚地行军。
——
一只只白骨的手爪攀附在墙壁上,骨骼磨蹭声刺耳又诡异,骷髅们循声而来,似乎并未觉察有生者到来,仅是用尽剩余的本能来到此地。
旅人迅速起身,按住你将要出鞘的银剑,你并非不解,回望一眼,不知什么时候起旅人的斗篷内散发着一股幽暗蓝光。
旅人将蓝光的源头丢出——水蜡烛在浑浊空气中扶光而落,亡者纷纷扑向蓝光,霎时间,骨片四处飞溅。
难以想象,这究竟是仇恨还是朝拜。
“不明之物的赐福替代了诅咒,尼尔霍斯的骨骼愈发庞大,以至于皮肉都开始崩解,躁狂的力量蒙蔽了他的双眼,使他无法认清伟大与渺小,不明所以地四处行军,周遭的军队都会躲避着他的疯狂,‘勇猛的王啊,您那不朽的伟力足以让铁骑人马俱亡,猛兽开肠破肚,堡垒坍陷毁灭,可您为何不看看这是否是我们的领土呢?’他的第二位妻子娜尔雅安向那片阴影祈祷‘不朽的主啊,赐给我视域吧,我需要它为您拨清迷雾’,娜尔雅安肚中的孩子化为血水,一根脐带被她排出体外,阴影中的存在让她将此代替神经链接在尼尔霍斯的双眼上,痴愚的领主恢复了澄澈,他在无人知晓的角落里点燃了蜡烛,如水般幽暗的蓝光下他想要去看清阴影,宛若窥视昏暗房间的幼童。”
旅人如是说,你并没有摆出实质性的态度。
令人感叹,仅此而已。
希芙拉的灭亡与此无关,至少这位愚昧的领主还没有疯狂到毁灭一切。
你冷眼看着还在蠕动的骸骨,将圣粉挥洒于阴湿空气中,腐臭与冷冽穴风交织,气滞流淌在鼻间。
“我宁愿你用臭虫剑处决我。”
旅人捏紧鼻子不满地抱怨。
探索似乎被卡入一个死胡同了,这里没有通道与天窗,只有庞大得堪称神迹的祭祀台。
“希芙拉是地底之城呢,我睿智的勇者啊。”
旅人笑笑靠近,似乎在试图说服你下坠于幽坑中。
你从石台下拾取一根蜡烛,用银剑磨蹭出火花,一缕新生的焰苗诞生于幽暗洞窟中,但不幸地是,你将它丢下了幽坑中。
“哐当……”
火焰依旧闪烁着,旅人趴在断崖上扯着脖子看。
“没有尸油,没有骨块,只有静默的碑文。勇者啊,我们好像真的需要下去看看呢。”
你没有说话,不顾旅人的反对,将绳子捆在他的身上,并缠绕在一根石柱上作为锚点。
“喂喂!不要这样!我已经认可了自己观光旅游团的身份啊!”
你没心情去听这近乎于无赖的理由,因为貌似有一群不欢迎你们的猎犬正在靠近。
——
无瑕者的触碰赋予它们亘古的时间,在幽黑空洞中寻觅着替死的生灵,悼亡者在祈祷,骷髅的头颅飞翔般携带着诅咒。
——
淡蓝色幽光于洞壁上浮现,似油墨滴于焦炭间粘稠。
骷髅头颅挣扎着脱离触手般的石钟乳,向闯入者坠落;宛若宫殿般的祭祀台下再次攀爬出白骨,这次不同的是,它们裹挟着盔甲含着锈蚀铁剑,狰狞地行进;用于祭祀的礼袍凭空悬浮,骨架支撑着,喷吐着火焰。
你后退一步,希芙拉的面孔正在一步步被揭露。
咳咳,这是原来的存稿,一直鸽子,我的错
最近一直在学写小说的方法,所以没时间更新
看到原来的帖子,毫无意义地堆砌词藻,确实很头疼,后面我会改的,只不过文风会很割裂。
但没事,我又得做回吟游诗人了
-
毋庸置疑~















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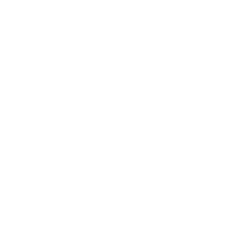

诶嘿